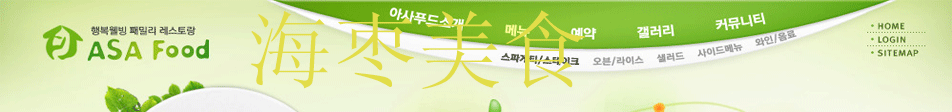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作者: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晓斌 引言 土地革命时期,由上海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是全国所有交通线中最重要的线路,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也叫“中央秘密交通线”。这条线路经上海、香港、汕头、梅州大埔、福建永定到达江西的中央苏区,全程约为公里。在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交通委员会和中央交通局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红色交通线在护送干部、输送物资、传送资金、递送文件和情报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而护送干部和人才进入苏区,成为这条秘密交通线的重中之重。 一、苏区干部人才的来源 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建设、巩固和扩大,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建立中央红色交通线,输送工作人员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中去,在当时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 (一)苏区干部人才的需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最缺的就是人才。地方党委缺少有文化、有思想、有觉悟的领导,红军部队缺乏连营职以上的有文化、有军事才能和战术素养的指挥员。特别是红四军入闽后,红军部队发展很快,一大批农民武装暴动队员和地方游击队整编为红军。而这些初始加入红军的人员大多觉悟比较低、文化不高,更没有军事素养,甚至不会站队列,不会拿枪,闹出许多笑话。苏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工作量的激增,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任务特别繁重,因此培养和建设这支红军队伍成了当时的紧迫任务。这点从周恩来年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可以证明:“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是闽西党的根本任务,中央切勿因人少而不派一人来主持此纵横四五百里拥有人口七八十万之闽西苏区。我意最好从中央各部中抽一人来此主持……”从另一份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也可体现:“此间自党代会后,在路线上却有一个转变,但干部非常缺乏,在各种工作都感困难,请中央加派大批干部来此,技术人员也缺乏得很。请尽量将学生及知识分子同志派来”。可见中央苏区对人才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急切、急盼、急需。[1](二)苏区干部人才的来源 各地苏区的干部,都来自五湖四海。中央苏区的干部队伍,主要来自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率领,从井冈山随红四军、红五军到赣南、闽西开辟根据地的同志;二是由中共中央派到中央根据地来工作的同志;三是从广西左右江苏区随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湘鄂赣苏区随红八军到中央苏区、从赣东北(闽浙赣)苏区随红十一军进入中央苏区工作的同志;四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参加红军的同志,以及被俘后参加革命队伍的同志;五是赣西南和闽西土生土长的,在革命斗争烽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同志。[2] 其中,由上海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来工作的同志,有一部分是留学苏联、法国等的回国人员,这些干部经过专业的学科训练,大多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他们有的担负起了中央和省、县及红军中的高级领导职务,有的从事无线电、医疗、文化、教育、兵工生产等专业技术工作。 留学干部归国后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的人数目前尚无准确的数字,但通过对已知人员的统计分析,来自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人数尤重。这两所分别设立于年和年的前苏联大学,与年开办在中国的黄埔军校一起,同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它们的创立和开办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莫斯科东方大学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图1),是苏联为培养苏俄东方民族和亚洲各国革命干部而创办的新型政治学校。年4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开设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隶属民族事务委员会,地址选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街。该校旨在造就苏俄本国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需要的全新干部,学制初为七个月,年起改为三年,设有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初期主要招收苏俄东部地区民族干部,后随形势发展,生源扩大到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学校分为苏联东方部和外国部,外国革命者均在外国部就读,下设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等7个班。中国秘密赴东方大学的学员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国民党始派遣青年赴东方大学。年以后,东方大学中国班继续开办,学生基本上是中共党员,另有小部分冯玉祥部队去的学员。年中,由于学生与校方的矛盾,东方大学中国班撤销,学生转到中山大学。[3] 图1:莫斯科东方大学(图片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东方大学开办的当年,中国就派去了学生,年的中国学员为36人。从年春起,中共旅欧支部的人员又分批转到了莫斯科。到年秋,共转了三批,加上国内去的一大批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班学员已达多人。刘少奇、邓小平、朱德、任弼时、聂荣臻、瞿秋白、肖劲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叶挺、刘伯坚、李富春、李卓然、黄火青等一批中共的杰出人物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该校为中国革命培训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优秀干部。年,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停办。 赴莫斯科求学的路线基本都是在上海乘船到海参崴,然后坐火车到莫斯科,行程约20天右。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涂作潮曾回忆:[4] 年10月的一天,支部书记林仲丹叫我带上洗脸用具,跟随他到了杨树浦自来水厂与恒丰纱厂附近的黄浦江边。在这里,由一只小舢板把我们送上了停靠在浦东的苏联轮船。在船上,林仲丹和一位苏联同志说了几句话后,便回转身来向我传达派我去莫斯科学习的组织决定。对于这一决定,我当然是高兴的,特别是能去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更是我毕生愿望。林仲丹和我谈完后,又亲切地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和我握握手,坐上送我们上船的那只小舢板,上岸去了。我站在甲板上,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不断地向他挥手,一直目送小舢板消失在夜雾之中,我才进了船舱。上船之后,我才知道同船去莫斯科学习的大约20人。胡子厚被指定为党的临时负责人。 开船后约一、二天,经过日本海峡的时候,碰上了日本检查船,它命令我们船停住,我们便都冒充船员在甲板上站队,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番。又过了一二天,船到了海参崴,来迎接我们的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在海参崴,我们大约住在“五一”倶乐部。过了10多天,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允许我们入学的通知电报,简单地检査了一下身体,主要检查有没有砂眼,便坐上烧木柴的火车到莫斯科去。记得车过赤塔的时候,沿途都挂满了红旗,是苏联人正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大约经过了15天的时间,我们才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 “东大”的校址在莫斯科“特热格亚,布里瓦尔”(译音)15号。校长苏曼斯基,教务主任布拉克。我所在的这个班都是工人。学的功课有:政治常识、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射击、爆破、密写技术等等。年下半年,我和王亚梅、陈哲夫、李福生进入“东大”国际班学习。班里有来自印度、土耳其、朝鲜、日本、蒙古等国家的同学。在这里学到年5月毕业。 涂作潮根据中央的指示于年1月又进入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归国后先在上海秘密装配电台,与李强等成功装配出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于年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成功进入中央苏区,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 不久,中央决定派曾三、伍云甫和我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出发前,李强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作为送行。 年3月,我们从上海随香港交通站派来接我们的交通员,乘法国邮船到了香港。由香港坐火轮到汕头,由汕头乘机帆船到了福建的三河坝。在三河坝,香港交通站的同志回去了,改由永定县地下党派来接我们的人护送。到永定县后,我们见到了地下农会负责人蔡端。蔡端找了三匹马,让我们骑马到了长汀,同行的还有一个残废红军。在长汀向有关部门取了路条后,便自己行动,最后到达江西兴国东固的坳上,我们被分配在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 年8月,瞿秋白同志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见到了列宁。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还曾在中文班主讲俄文、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课程。归国后,瞿秋白于年1月11日离开上海,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于年2月5日抵达瑞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七一前夕,革命烈士瞿秋白独女、岁高龄的瞿独伊被授予党内至高荣誉“七一勋章”。她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在解放后赴莫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其间多次担任周总理和中国访苏代表团的翻译。作为赓续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相信瞿秋白在莫斯科的经历也深深地影响了瞿独伊(图2)。图2:瞿秋白(右)、瞿独伊(中)与杨之华(左)一家三、莫斯科中山大学 随着形势的发展,现有的东方大学中国班以及中国国内的黄埔军校已不能满足需要,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办一所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为了纪念于年3月逝世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将这所学校定名为“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习惯上称之为“莫斯科中山大学”。 年10月7日,在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成立,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选拔学生赴苏学习。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限制,只在广州进行了公开招考,其他地区由组织上秘密推荐,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中共党组织完成的。据统计,从年秋冬到年初春,第一期学生多人,先后分四批出发,陆续到达莫斯科。其中三批是由国内选拔推荐,集中到上海和广州后赴苏的。还有一批是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赴苏联的勤工俭学学生。从此,东方大学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任务,就分移给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教学目的,在于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熟练的政治工作干部,因此在教学和课程设置上力求理论与实践并重和因人而宜,同时借鉴东方大学业己积累的经验。[5]图3: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现状 莫斯科中山大学从年成立,到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至年停办,共有四期学生,前后共约有名,其中包括年东方大学中国班撤销后转入的多人。 与东方大学中国班不同的是,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既有中国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员;既有青年学生,也有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如邓小平、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何叔衡、杨尚昆、李伯钊、左权、王稼祥、张闻天、刘英、吴玉章、徐特立、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伍修权、危拱之、凯丰、秦邦宪(博古)等人,都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值得一提的是,漂留海外的共同经历,也成就了不少革命夫妻,如张闻天与刘英,杨尚昆与李伯钊等。 李伯钊于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年毕业后,留校做翻译工作,年与杨尚昆在苏联结婚,年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年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到闽西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她赴苏联之前曾因在上海做共青团工作被国民党当局监禁两个多月,出狱后即被派往苏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6] 怎么走,跟谁走,当时全没有告诉我。一天晚上,有个车子来了,来人叫我赶快上车。汽车开到黄浦江边,一条舢板把我们逮到了吴淞口。在那里,我们上了一条苏联船。我们住的是比较好的船舱,但我是头一次出国,有些害怕,他们说到海参崴有人接我。船颠簸得很厉害。我吐的一塌糊涂,有个男同志一路上照顾我,我不好问他姓什么,是干什么的,我要吐,他拿来东西帮我接着,在船上天天吐,有时一、两天不能吃一点东西。后来不怎么吐了,可以吃点东西,但还是不能起来,只能躺着,到了海参崴,他们说“已经到了”,我以为到了莫斯科,原来是到了海参崴。到船舱外边呼吸新鲜空气,感到特别舒服。下船后来到一家旅馆,那旅馆很好,帮助找大夫给我看病。我在旅馆里看到很多同志,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这些人在船上我都没有见过。后来我们相互认识了,现在记得的有这么几个人:张仲实,上海大学的学生俞季女、胡建三,上海大学附中的樊警吾、陈西媛。还有一些已经记不清了,他们有的是上海大学的,有几个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在海参崴旅馆休息了一天,规定不准出去,不准和外人接近,上厕所也要告诉翻译。 从海参崴到莫斯科是坐火车。苏联内战以后,相当困难,火车没有煤炭,烧大块的木柴。我们都下去帮助把木柴搬上火车。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我们在车上没有吃的东西,要到站以后才有卖的,但也只有玉米,连面包都没有。火车的速度很慢,走好几天才见到一个站。到了站就赶快下去买东西,赶早才能买到面包。钱是组织上给的,每天给一些。当时最困难的是茶水。干面包很硬,要用开水泡,没有开水干吃很困难。茶水到预定的站才有,每人只能装一壶两壶,有一定的限制。在火车上,我们看见窗外正在行军的苏联红军没有靴子。用碎皮缠在脚上当鞋,这是内战的痕迹。尽管当时苏联这么困难,但我们学生还是很开心,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人人都很兴奋,一路上唱歌,互相介绍,互相认识,互相关心,最困难的是张仲实,他的眼镜高度近视,上下火车都要人扶,就这样大概坐了一个月的火车才到达莫斯科。 我们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会派人带着苹果、面包来迎接我们这些新同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都要编号,我是号。学校里有米饭吃了,伙食也挺好,同学们很热情。可是语言不通,不懂话,我们首先要学会说俄语的编号,因为你吃饭、洗澡等一切,都要先报你是多少号。学校专门有人来教我们。房子住的也好,还发了大衣、外衣、毛衣、皮靴。那就是大学生的待遇了。因为看不懂俄文,生活中有困难,学校就先教我们生活语言。学生分一班、二班、三班。邓小平在一班,上海大学教经济学的沈志远的妹妹沈连春在二班,我在三班。 …… 一九三〇年冬天,我从莫斯科回到祖国,记得到上海那天正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时尚昆和张闻天也回来了,都是走北面交通线回来的。我到上海后是做工会工作,在法兰区香烟厂从事工人运动,大概有二、三个月时间。那时上海情况很紧张,我们又在苏联学习过,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后来中央决定让我们到苏区去。苏区红军队伍也很需要干部。 我去苏区是由一位年轻的交通员带路,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忘了,走的是香港这条路,经过大埔、青溪,那里有个交通站,邓小平等同志都是经过这个交通站到苏区的,那时大概正是二次“围剿”,路子断了,国民党又占领了汀州,不能去中央苏区,我就在闽西苏区留下。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鼎丞,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是邓发,闽粤赣边军区参谋长是肖劲光。 李卓然同志于年初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赴法勤工俭学,后转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与同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的肖劲光是同学,他俩回国后于年同时进入中央苏区,根据肖劲光回忆,他们在香港机智地通过一条白手帕躲过检查[7]。与同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伍修权同志年通过几块手帕“智过”交通线几乎异曲同工[8]。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我(即肖劲光)和李卓然同志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临行前,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用密写药水在一条手帕上为我们写了介绍信,由卓然同志带在身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猖狂,党在白区的组织不少遭到破坏,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十分谨慎。离开上海时,我化妆成商人,李卓然同志化妆成教师,经过数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来到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租界地,虽然也危险,但由于它的自由港的地位,过往的各国人众多,客观上比较好隐蔽。我俩与交通员接上头,住在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上安排去汕头。一天,我俩在街上走,看到一个小书摊上摆着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就买了下来。因为我们从苏联回国的时候,为了躲避层层哨卡,基本上什么书都没有带回来。看到合适的书,就想买一点,准备日后工作之用。 不料在过卡子时,不知为什么,英国巡捕把我们扣下了,当时这本书还在我手中拿着,扮作教师的李卓然同志马上很机警地把它拿了过去。因为我是扮做商人的,这本书我拿着显然不合适。过了一会,巡捕来搜查我们。先搜了我的身,什么也没有搜到,接着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大米生意的。在搜查我的时候,我看到李卓然同志从容不迫地拿出那条写有介绍信的白手帕,使劲擤了一下鼻涕,卓然同志有鼻窦炎,这件事办得既自然又贴切。当英国巡捕搜他的身时,看到这个沾着鼻涕的脏手帕,厌恶地把它扔在地上,结果自然也是什么也没搜出来,就挥手让我们走。这时,卓然同志很坦然自若地把手帕拣起来放进口袋里走了。李卓然同志表现得是那样的机警、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遇险以后,我们的行动更加谨慎了。过了几天,党的交通员送我们从香港到了汕头,沿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经大埔进入闽西苏区。我留在了闽西,李卓然同志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奔赴赣南中央苏区。四、红色国际交通线 其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建立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先后在内蒙古境内开辟了三条红色国际交通线——经满洲里出境通过亚欧大陆桥前往莫斯科、穿越阿拉善戈壁走“定库驼道”出境、途经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到达乌兰巴托。[9] 第一条红色国际交通线是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穿越西伯利亚平原,经由莫斯科通向欧洲各国,这条横穿亚欧大陆的铁路被称为第一亚欧大陆桥。交通线一端通过满洲里连接到国内,另一端则通向莫斯科。通过梳理赴苏的留学生出国之路,大部分都是走这一条(见图4)。 第二条红色国际交通线被称为“定(定远营)库(库伦)驼道”,它穿越阿拉善境内的茫茫戈壁,来往于苏联、蒙古和中国内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定库驼道”成为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和中国共产党人进出境的密道。邓小平在年底从莫斯科回国走的就是“定库驼道”,而李伯钊回程说的北面交通线应该也是指这一条。 第三条红色国际交通线是年以后,红军到达陕北后开辟的一条新的交通线:由陕北三边地区经伊克昭盟(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桃力民(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至大青山,与蒙古国、苏联取得联络。 这三条红色国际交通线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国际联系在一起,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邓小平的归国路线:“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换乘汽车,到达当时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等了一个短时期后,由于车辆容载的限制,首先派出三人为第一批先遣队,这3个人就是共产党员邓希贤(邓小平)和王崇云、朱士恒两名共青团员。他们换乘的是苏联给冯玉祥部队运送子弹的汽车,一共三辆,都由苏联人驾驶。”进入阿拉善境内后,由于沙漠阻路,他们“骑骆驼,整整走了8天8夜,才算走出了这看似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海”,到达定远营(今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再从这里奔赴革命前线。[10]图4:红色国际交通线之第一亚欧大陆桥(图片来源: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教育基地展厅)五、余论 除了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两所主要学校外,还有一部分人也在苏联其它学校学习工作,如陈赓同志于年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李维汉同志于年赴莫斯科学习。陆定一同志于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外,也有一部分先进分子远赴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如周恩来同志于年就赴日本求学,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年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成仿吾同志早年留学日本,年又赴欧洲学习。李六如同志于—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 当然,本文列举的留学生(见附表),只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千名留学生中的极少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的留学生在学成归国后,抱着救国图存的革命理想,冒着生命危险毅然穿过重重封锁线,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来到中央苏区,他们中大部分人的名字,至今可能无法一一明确,但他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热血甚至生命,与一路上为他们保驾护航的交通员一起,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儿女心中。附表: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的留学生统计表 (注:该表格数据仅为阶段性成果,相关信息将根据研究进展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年12月 [2]胡国铤主编:《共和国之根》,中共党史出版社,年5月,第50-51页。 [3]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年。 [4]《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31-32页。 [5]黄纪莲:《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年第5期。 [6]李伯钊:《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年,-页。 [7]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年,76-77页。 [8]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9]《在中俄蒙边境,三条“密道”见证峥嵘岁月》,《参考消息》,年5月26日。 [10]邓榕编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年。转载:南粤古驿道网责任编辑:彭剑波江家敏End 广东省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协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