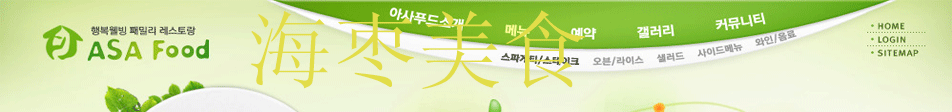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在我感觉满洲里真是挺小的,土地面积平方公里,比丹东还要小一点(丹东市区是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万,还不到丹东市区人口的一半(丹东市区人口69.7万),所以在满洲里你很难感受到熙熙攘攘的热闹繁华,可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满洲里还是很有特色的地方,我愿意为它记上一笔。印象中最深的是满洲里的云,平生没见过那么低的云。在我乘坐车去草原的时候,车窗外的云大片大片的,仿佛我伸手就能摘到的样子,我拍了些视频发到朋友圈里,大家都问:云是假的吗?云是真的,它们那样肆无忌惮地悠悠地飘着,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任凭阳光把它们的倩影留在广袤的草原上。这就是蒙古人眼中的长生天。我到满洲里的时间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傍晚······从机场到酒店迫不及待的欣赏着夜景······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了草原······我知道蓝色代表草原是因为曾经读过一篇小文,题目是《蓝色敖包的郁闷》,文章讲了敖包,讲了长生天的信仰,我复述的也许没有原文那么好,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原文看一下。曾经在大元朝民族是用颜色来划分的:蓝蒙、红汉、白回、黑藏、黄色目(色目大约代表其他的意思,指蒙、汉、回、藏之外的其他各色名目之人)。蒙古族喜爱蓝色,崇拜蓝色是源于久远以来对长生天的信仰,长期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深深知道草原是多么珍贵,草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经破坏很难复原,保护草原成了每一位草原人的使命,他们传唱的是嘎达梅林的故事,为了草原而战斗,为了草原而牺牲。 在我们去往呼伦湖的路上,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草场,它们同属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一部分,那里也有人生活,可是几乎看不到生活垃圾,草原人是不会随便丢垃圾的,因为牛羊吃了会生病。草原人知道草原并不属于他们,草原属于生活在这里所有的“精灵”,就像那本著名的小说《狼图腾》告诉我们的一样,在草原上即便是凶狠的狼群也是这条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存在。一切都是长生天的巧妙安排,“顺者兴,逆者亡”。祭祀长生天的地方叫敖包,就是《敖包相会》歌唱的地方,那里可不是专门用来约会的。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在我跨马扬鞭经过敖包的时候,我会下马,从左向右绕三圈,祈求长生天的保佑,如果附近有石头,我还会为它添上一些石头,如果我有哈达或者马奶酒,我会献上这些祭品。 呼伦湖是内蒙古最大的湖,它与贝尔湖上下呼应,才有了呼伦贝尔这个美丽的名字,呼伦和贝尔在蒙语里词义相近,呼伦是“雌水獭”,贝尔是“雄水獭”,所以有人说它们是夫妻湖,也有人说它们是姊妹湖。不管它们是夫妻还是姊妹,它们都是呼伦贝尔草原的灵魂,没有它们就没有富饶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还有一个小名叫“达赉湖”,蒙古语“海”的意思,湖边最负盛名的大概是全鱼宴,据说有几道菜很有名,由此可见蒙古人不吃鱼的说法有待推敲。 我们在满洲里的第二站是国门景区,去往国门景区的路上还会经过满洲里套娃广场,这在满洲里也是个标志性的广场,一进国门景区首先经过的是火车头广场,广场上的陈列的是年日本生产的“亚细亚号”蒸汽机车,说起“亚细亚号”大连的小伙伴一定不会陌生,它的生产厂家可是日本占领时期咱大连的沙河口机车厂哦。另外据说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是乘坐这台机车牵引的火车出访苏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车上的编号是“”。“18”代表的是满洲里到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的距离,即18里。“61”是代表毛主席在满洲里期间曾对驾驶这辆火车头的司机长说过的六句话:一定要与苏联同志搞好友邻关系,一定要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的相互团结,一定要保障军用列车的安全,一定要多学文化,一定要克服天气寒冷带来的困难,一定要注意身体。在火车头广场就能看到国门,国门下方就是建于一百多年前的东清铁路,就是因为它的建成,才有了现在这座因车站而得名的边境小城——满洲里。 满洲里的街道是用数字排的,一道街、二道街一直排到五道街,我大概用了小半天的时间,把这些街道转了一遍,每条街都不长,街边的建筑融合了俄罗斯、哥特和蒙古族的特色,到了夜晚,在华灯的映衬下,更添一种别样的风情。在路上,不时会看到挂着俄罗斯牌照的车,我不知道他们最远能开到哪里。总体来看满洲里的生活很轻松,连机场的工作人员看上去都好像没事可做,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这样的轻松自在,不妨去一次满洲里。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