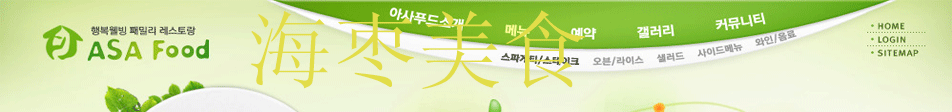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人民日报社市场报网络版《民声面对面》文摘(作者:许华)关于姥爷张逸仙的那些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我大多是听舅舅讲的。舅舅曾讲过多少遍,已经记不清了;我曾听过多少遍,同样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正值青春年少时候的我,听了舅舅的讲述,从心里觉得姥爷象演过的那些英雄,英武魁伟、顶天立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顽强斗争、不惜生命……崇敬之意油然而生。可是,每每讲起自己父亲的故事,舅舅脸上的表情与我却大不同。他那神色、那语调里,除了自豪与荣耀,还有悲壮、凄凉,甚至痛楚。 舅舅的讲述,几乎每一次都是从那个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开始…… 一、 年隆冬时节。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一列火车艰难地喘息着,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缓缓前行。十多天来,这列从莫斯科开出的火车一直在向东行驶,向东、向东,离中苏国境交界处的中国边陲重镇满洲里越来越近了。 冬夜漫长。漆黑无边的雪野上看不到一丝生机,只有从列车车窗里透出的方格样的昏黄灯光,排成一字向前慢慢移动着。已是凌晨时分,车厢里的乘客差不多都沉沉睡去。张逸仙却毫无睡意。他用大衣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抵御着不时由车门缝隙袭击而来的寒气。他把头靠向座椅后背,紧闭双眼,只是假寐。他感觉到,火车离中国边境越近,自己的睡意就越来越少,几乎整整一夜,张逸仙就这样头靠椅背、紧闭双眼地坐着,静静地听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均匀的金属声响,脑海里却是浮想联翩:自己四十岁人生走过的道路,与兄弟同志们在深山密林中抗击日寇的烽火岁月,还有近半年来在莫斯科接受的训练和使命……像过电影、如放幻灯,一幕幕、一帧帧清晰地闪现,继而渐渐隐去,再闪现,又隐去…… 年7月1日,张逸仙生于山东潍县寒亭(今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兄弟七人,他是老五。当时,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张潼是晚清举人,做过十多年教书先生,不仅颇有才学,还富有民主意识和爱国思想,是同盟会会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逸仙兄弟们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民主爱国思想的熏染。还在张逸仙少年时候,在日本读书的大哥就时常邮寄一些诸如《民报》、《天讨》之类的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回来。当时张逸仙尚在小学,还读不懂这些书刊上的文章,四哥便拿来读给他听,边读边讲。讲清朝政府如何腐败,讲我中华已经到了危亡地步,热血男儿自当奋发自励,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于此,张逸仙脑海里,民族革命思想渐渐萌生。 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波及山东,时任寒亭小学校长的张逸仙与一群热血青年拍案而起、振臂响应,组织集会,宣传群众,成立了寒亭国货维持会,抵制、查抄日货,以此唤醒农商,一时间轰动整个潍县东部地区。然而此后不久,张逸仙的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经济骤然变故。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放弃教书职业,跟随张伯言、曹星五、于祖黄等几位乡邻父兄来到哈尔滨阜济林业公司工作。 阜济林业公司的创办者张伯言、曹星五、于祖黄都是留东革命党人。他们这个林业公司,表面看是个实业团体,内部却聚集了许多倾向民主革命的革命党人。张逸仙置身其间,耳濡目染,逐渐开始想走一条“实业救国”之路。此时,也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社会主义思潮已在中国兴起,哈尔滨的一些书店里,已有马列主义小册子出售。张逸仙梦想着“实业救国”的同时,又通过这些小册子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学说。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张逸仙的“实业救国”梦。日寇进驻哈尔滨,逼迫张伯言合营阜济林业公司,图谋吞并。张伯言断然拒绝,只身返回潍县老家,不久便因悲愤积瘀成疾,含恨而死。 正值壮年的张逸仙目睹了日寇的烧杀掠夺,民族的奇耻大辱让他义愤填膺。宁死不当亡国奴!倭寇刺刀之下,苟且偷生都难,何谈实业救国?张逸仙毅然将多年积蓄的钱款财务倾箱倒箧,拿来购买枪支弹药;把愿意抗日的亲朋好友、散兵游勇,甚至土匪胡子纠合起来,打出了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的旗号,凭着一腔爱国救国的激情热血,在莽莽深山密林之中与日寇展开了真刀真枪的殊死搏杀,也曾有攻破战绩。然而,张逸仙清醒地看到,这支东拼西凑拉起来的武装,是一支很不正规的队伍,无论人员素质或武器装备而言,都无法与日军长久抗衡。势单力薄,必须有后援之力。为长远计议,张逸仙只身远赴关内,企图通过各种关系寻求实力支援。此时,他的身份是抗日救国军第十一路军总参议。 他先是辗转北平、天津,通过朋友介绍见到了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对张逸仙的抗日义举和爱国热情给予了相当的奖许和慰藉,临别时还送上三百元路费。然而对于军需物力援助,却无实质表态。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东北各地找到少帅府上请求支援队伍太多,都是抗日救国,且番号各异,良莠参差,使得张学良难下决断,干脆一律善待敷衍。 离开平津,张逸仙南下金陵。在南京,又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名叫方觉慧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听张逸仙说明来意,这位方中委答应将此事请示蒋介石,让他静候回音。在等候回音期间,张逸仙去了上海,看望弟弟张鹤眺。见到弟弟时他才得知,弟弟张鹤眺已是中共中央文委、左联党团书记,化名叶林,亦称耶林,周围的人都称他“叶先生”。得知张逸仙此番南下意图,叶林与他彻夜长谈,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对他想求得国民党上层对自己的抗日武装给予支援的想法很不以为然,说那是竹篮子打水,是凭空臆想。但是,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其它原因,叶林最终业没有给哥哥指出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抗日救国道路,这使得张逸仙有些茫然。辞别弟弟,回到南京,又见到方中委,也听到了蒋介石的答复:“此事暂从缓议。”抗日救国的火热激情,遭遇了“暂从缓议”的一瓢冷水,张逸仙开始体会到,弟弟叶林说寻求国民政府支援抗日是“此路不通”,不无道理。南北奔波数十天却毫无结果,无奈之中只得踏上返回东北的旅程。然而,此时他还不知道,在自己梦想开辟的抗日道路上,他已经是在踽踽独行了。 原来,张逸仙进关之后,他的那支常在呼兰一带活动的队伍,遭到日军严密围剿。在受了残酷的军事打击且无后力之援的情况下,溃不成军,待到张逸仙返回时,队伍已经人马四散,不复存在了。于是,张逸仙又悄悄潜回哈尔滨隐蔽起来。 虽然迷茫困惑,而且连遭挫折打击,但张逸仙心中抗日救国的炽烈火焰却未熄灭。在哈尔滨期间,他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寻找救国报国的路径。不久,在与一些朋友的交往中,他认识了一位叫杨殿坤的人。张逸仙与杨殿坤算得气味相投,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彼此间谈论最多的就是民族危亡、国家命运和个人的理想抱负。言谈理论之中,张逸仙深得杨殿坤启迪。后来张逸仙终于知道,杨殿坤是共产党员,也曾领兵打仗,身上还留有四五处枪伤疤痕,于是对杨殿坤愈加钦佩。 年初春,张逸仙欣然接受杨殿坤建议,决定去苏联学习。虽然他不知道去苏联学习的具体科目和内容,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会有希望,自己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救国报国的理想。 杨殿坤通过一条神秘地下交通线的联络、介绍和筹备,张逸仙几经周折,终于在年春夏之交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从踏上征途的那一刻,他心中就牢记着杨殿坤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我与你已经不单是朋友,而是同志。” 二、 距莫斯科西北方向二十几公里,有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山顶上,密林高墙中遮蔽着一幢楼房,这里就是张逸仙学习的学校。学校里的学员来自多个国家,有德国人、波兰人,但多数是蒙古人和中国人。原来,这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特工训练基地,从踏进这座楼房起,张逸仙他们便有了一个新的特殊的身份——共产国际红色特工。 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是由列宁于年倡导并组织建立的一个全球性政治组织,被称作:“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国”,是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及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军事斗争的指挥部,影响巨大。此时,共产国际的领袖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 这所学校的目标,就是培训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反法西斯特工战士,即红色特工,张逸仙就是其中之一。学员们总的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十八天,由莫斯科派来的教官授课。授课教官每天早晨从莫斯科来,教完一天的课程,晚上返回莫斯科。而每个学员,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准迈出校门一步。还有,学员们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到此之后都由校长给每个人起一个新名字,原来的名字只有你自己和校长等极少几个人知道,学员之间绝不允许相互询问打听。张逸仙的新名字叫“古斯达夫”,当时连张逸仙自己也不曾想到,不久之后,这个“古斯达夫”竟成了一个令华北、东北一带侵华日军颇感头痛可恐惧的名字。 学员们学习的课目有:爆破(主课)、射击技术、军用化学、驾驶汽车、游击战术、秘密工作和政治。除秘密工作和政治两门课程是主要在教室授课外,其它几门课目都是以现场演示讲解和实际操作为主。 转眼间,三个多月艰苦紧张的学习训练生活结束了。张逸仙他们这批二十几名学员,每个人都以各科成绩优秀通过毕业考核。更让他们激动的是,在此期间,他们全部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成为受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反法西斯战士。毕业之后,他们将各奔东西,走上反法西斯战斗的前沿。学校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毕业仪式为学员们壮行。大家围坐在摆满美酒佳肴的长长的餐桌前,首先聆听校长讲话。校长慷慨激昂地讲国际形势,讲学员们即将担负的神圣使命和光荣任务,最后给予大家一番鼓励。接下来是学员们逐个表态发言,张逸仙只讲了一句话:“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巧说。”酒足饭饱之后,校长又与学员们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学员离校是分组分期出发的,张逸仙与另外两位中国同志为一组,校长指定张逸仙为组长。临行前,每人必须写一份“誓愿书”交给校长:1、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3、无论遭遇任何危险,绝不泄露组织秘密。在必须遵守的纪律中,有一条让张逸仙难以释怀,那就是:回国之后,必须断绝与本国共产党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的所有联系,不允许跟自己曾经一道工作、战斗过的同志朋友再有任何来往。尽管想不通,但纪律就是纪律。 就这样,张逸仙又登上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驶向东方的列车。来时春风送暖,此刻却是地冻天寒了。 黎明时分,列车停靠在一个小站,此处离中国的满洲里不远了。张逸仙一行三人下车之后,又爬上一辆卡车——这是苏联组织上派来接他们的专车。卡车在茫茫雪原上颠簸着,张逸仙他们在刺骨的严寒中瑟缩着。半夜时分,卡车在不知什么地方的一所小房子前停下,张逸仙三人在这所房子里稍事休息,并且吃了一天当中第一顿热饭,然后在一名苏联红军军官的带领下又上路了,这回是徒步行进。夜色深沉,他们紧跟在苏联军官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没有语言交谈,也辨不清走向何方,只有一种感觉:冷!天蒙蒙亮时,苏联军官停下脚步,指着远处一片朦胧可见的房屋轮廓说,那是中国小镇扎兰道尔,也是一个铁路小站,这里没有日军瞭望哨,穿越过境比较安全。然后向三位中国人道别,转身返回。 张逸仙他们悄悄回中国境内,天已大亮。又过了三天之后,张逸仙到达哈尔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右脚的三个脚趾已被冻得乌黑坏死,医院动手术割掉。待他康复出院,并按照上级预先指示到达天津接上关系的时候,已经是年3月的下旬了。 三、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日本法西斯加紧了对东北三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巩固后方以便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东北的抗日斗争环境极为困难险恶。这时的天津,各种政治势力杂居交错,反而使共产国际特工组织的隐蔽相对较为容易和安全一些。 张逸仙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反帝情报组织满洲第二组副组长,他的直接领导是一名常住在天津苏联领事馆、会说英语的德国人。由他下达给张逸仙的主要战斗任务是:想方设法破坏日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设施和后勤储备,以阻挠日本实施北上西进入侵苏联的阴谋。因为当时,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时常在中蒙边境联合看守军向苏联发起小规模军事挑衅,窥测苏联的外交反应和军事实力,日益显露出向北进犯的侵略野心;另外,负责发展吸收新同志,为组织内同志送发活动经费。 在接上关系、领导任务之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张逸仙就在东北各地发展了一批新同志,并将在苏联学到的爆破等特工技术教授给他们。同时利用各种渠道暗中购买积聚制作炸药的化学药品和器材,秘密侦察日军在各地战略设施的位置和防守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计划和准备之后,“古斯达夫”开始行动了。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向关内大举进犯。随着展线不断拉长,日军所需的军火和战略物资的运输需求日益增加。初冬时候,张逸仙手下的同志侦察得知,日军正在加紧修建通化至辑安的老岭山隧道。这条隧道一旦贯通,日军的军需物资由北朝鲜通过铁路运往中国前线将更加方便快捷,这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无疑是一个很大威胁。张逸仙听到汇报,果断决定,立即炸掉这条隧道。他选定四位同志,自己亲自带领,每人身上都背上沉重的炸药、雷管和引爆装置,这个五人爆破小组趁暮色钻入密林之中,向老岭山进发。他们翻山越岭到达老岭山隧道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五个人在隧道口附近隐蔽下来精确观察,隧道正处在竣工收尾阶段,洞内洞外静悄悄的,没有干活的工人,只有两个伪军肩扛步枪在洞口来回走动,也悠闲得很。真是天赐良机!张逸仙几个人悄悄摸上去,干掉了两个伪军。随即,张逸仙吩咐其他四位同志进洞安放炸药,自己拿起伪军的步枪在洞外警戒。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由远而近,他迅速隐蔽,沿山路望去,只见一辆日军卡车缓缓开来。汽车上,除了开车的日军兵,两侧车门踏板上各站一名持枪日军士兵;车厢里站满了中国百姓,他们是被抓来修隧道的民工。见此情景,张逸仙急了:如果汽车开进隧道,且不说自己的同志有多危险,即是考虑到几十名民工的生命安全,爆破也不能实施了,岂不功亏一篑!他当机立断,举起步枪对着汽车“砰”地开了一枪。汽车戛然而止三个鬼子跳下车来,藏在一块山石后面,车上的民工乱作一团。张逸仙趁机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抗日联军,你们快跑吧!”车上的人们一听,纷纷争先跳下,夺路而逃。一个鬼子企图阻拦,张逸仙顺手一枪将他撂倒。另外两个鬼子见状,以为遭遇了抗联大队人马,也不敢还击,猫着腰沿山路逃了回去。这时,进洞的四位同志已经将炸药安放完毕,跑出隧道。张逸仙用力作了一个手势,同志们立即按下起爆器,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地动山摇,整条隧道几乎全部塌陷下来…… 大连甘井子油厂,是日军在东北、华北一带最大的汽车和飞机燃油供应基地。年4月初,张逸仙接到上级密令:炸掉甘井子油厂。他将任务分派给秋世显等三位同志执行。秋世显是清末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的侄孙,是张逸仙发展的组织骨干成员。秋世显三人接受任务之后,立即对甘井子油厂进行细致侦探,最终在如何将炸药带进厂区这个问题上卡了壳,一筹莫展。原来,日军对油厂戒备极严,对每一个进厂上班的中国工人,都要进行几乎裸体式的搜身检查,天天如此,班班如此。在这样严密野蛮的检查之下,想把炸药带进厂区,根本不可能。面对难题,张逸仙破费了几天心思。他反复琢磨在苏联学到的化学炸药配方,将其改进,终于制成一种特殊炸药。这种炸药在露天环境中经充分氧化后会自然爆炸。然后,张逸仙又将炸药制做成一块块“肥皂”,分发到几个工人兄弟手中——工人们带肥皂、毛巾进厂上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日本人对此毫无戒心。于是,一块块“肥皂”被工人们堂而皇之地带进了油厂,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到了油罐下面、油桶堆里……4月15日晚上八点多,甘井子油厂堆放油桶的露天仓库突然起火爆炸,紧接着是几个油罐、油品库也连锁反应、燃起大火。爆炸声声‘烈焰腾腾,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日军有油桶接连爆炸,腾空而起,又砸向地面,火势极为凶猛,救火人员无法靠近。日本鬼子眼睁睁看着这场大火燃烧了十六个小时,只剩下捶胸顿足的份儿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甘井子油厂处于瘫痪之中。 此后数月,日军在大连及周边地区的十几处石蜡、油漆和化学工厂、仓库相继莫名其妙地爆炸起火,化为废墟,不仅让驻东北日军惊慌失措,甚至震动了日本内阁,责令严查、限期破案。终于,日本人在一处爆炸现场查找到半块没有氧化干净的“肥皂”,由此认定,一连串的爆炸起火事件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组织所为,他们称这个组织为“纵火团”,而东北的老百姓则在暗中奔走相告,说这是“火神爷”干的。 不久,“火神爷”再次光临日军周水子军用仓库。 自从日军发现“肥皂”炸药以后,对在所属工厂、仓库工作的中国人试行更严厉的盘查,任何人一律不准带肥皂上班,违者严惩。如此一来,“肥皂”又行不通了。张逸仙组织中有一名同志是周水子仓库的工人,他发现许多工人上班时带的午饭是煎饼卷大葱,而日本兵对工人手里的煎饼大葱不做检查。据此,他向张逸仙提出一个大胆设想:把大葱的下半段葱白掏空,装进化学炸药,卷在煎饼里带进仓库。张逸仙批准了这个方案,经试验,的确可行。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周水子仓库上工的汽笛刚刚拉响,就见一个工人一边啃着煎饼卷大葱,一边匆匆忙忙奔向仓库大门,即是在日本兵脱下他的衣裤进行检查时,他嘴里也没停止咀嚼,一阵阵大葱气味儿让日本兵不时地皱皱眉头。很快检查结束,那个工人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当天黄昏,周水子仓库燃气冲天大火,即将运往前线的几十吨食品和上万套毛料军装化为乌有。日本鬼子做梦也想不到,引发这场大火的,竟是卷在煎饼里的两根大葱。 从年到年的六年多时间里,张逸仙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实施了一百多次爆破燃烧行动,使侵华日军的战略物资及设施损失惨重,有力配合了关内外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军心大振,民心大振,日本侵略者惶惶不可终日。日本关东军情报组织在写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发出如此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料及其它贵重物资被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四、 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正处于异常惨烈的战争相持阶段。为了扼制日军在中国南方的疯狂攻势,张逸仙和同志们研究拟定了又一次重大行动计划:爆炸日军大连飞机场及其燃油仓库,并且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然而就在这时,张逸仙接到上级密令:立即停止一切行动!他顿感疑惑迷茫:为什么?当然,这个“为什么”只能在心里发问,命令必须无条件执行。张逸仙分别向各小组的同志发出电报指令:停止行动! 此刻,张逸仙和他战友们还不知道,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的变化,以及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内外交政策的利益,他们这些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的命运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当初,苏联派张逸仙等一批红色特工遣回国内的主要目的,就是牵制日本北犯苏联的战略野心。基于此,每当日军在中、蒙、苏边境挑衅行动频繁时,红色特工们接到的来自于莫斯科的、旨在摧毁日军后方战略基地的命令就多。相反,如果边境线上稍有安宁,莫斯科的命令就少。 从年9月起,情况开始悄然变化。 年5月,在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处的诺门军,以日本关东军进攻苏蒙联军为导火索,爆发了著名的诺门军战役。此役历时四个多月,最终以苏军名将朱可夫指挥的苏蒙联军大获全胜,日本关东军付出伤亡五万余人的惨重代价而告结束。诺门军战役使日军彻底放弃了向北方扩张的战略计划,转而“南进”。此后,苏日双方在二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直至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 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把曾一直打算“抽手旁观”的美国彻底拖入二战战火。从此,日本军队的作战目标几乎全部瞄向中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在北方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微乎其微,使斯大林不再有遭到东西夹击的忧虑,专心对付德国法西斯。 正因为国际形势发生的这些变化,尤其是到了年,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以此为标志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斯大林为了打消欧美各国对“共产主义红祸”的顾虑,促使英美联军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及早结束苏联在欧洲大陆独自抵抗德军的局面,作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解散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络和通讯渠道即刻切断。群龙无首,孩子没了娘。不久,张逸仙和他的同志们纷纷四散而去,各奔东西,却不知何去何从。这些年来,作为共产国际的特工,他们不得与国内任何政党、组织和军队有丝毫联系,他们的身份无人知晓,无法认可。他们的战斗行动可以惊天动地,却无人知道、也无人证明是他们所为。何处是他们的归宿? 张逸仙又回到黑龙江呼兰一带,希望能找到十几年前的同志和战友,无果而终。为了生计,他在一个村子里做了私塾先生。后来,因战乱日甚,私塾办不下去了,张逸仙没了生活来源。不得已,他费尽周折,辗转数月,终于年3月回到山东寒亭老家。 此时家里,妻子已经病逝,大女儿也出嫁了,张逸仙谋到一份中学教室的工作,带着两个十三四岁的儿子勉强度日。然而他壮心不已,他一直在等待着、寻找着机会与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是苏联共产党党员,因而也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毕生。 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逸仙也曾设法联系到当时驻潍县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只是根本无法证明他过去的经历和身份,党组织不能吸纳他,部队也不可能让一个年近五十的人参军。就这样,张逸仙一直在中学教师的职位上迎来了新中国诞生。 年,肃反运动开始。张逸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被怀疑为“外国特务”,在遭到一次抄家之后,进了肃反学习班接受审查。在学习班里,张逸仙一遍又一遍地写了有关自己身世历时的说明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接受问询、谈话、审查。最后又将他的材料上报省委肃反小组,得出结论:“该同志不列入肃反。”但此结论不对外公布。 肃反学习班结束,张逸仙被安排到远离家乡一百多里的平度县一所中学当老师。年,他六十岁了,要求退休,教育部门以他参加革命工作不足十年为标准,发给他一年的工资作此后养老终生的费用,再无往来。那时候,张逸仙已是体弱多病,没有了工资收入,没有了公费医疗,家境原本就非常贫困的他,无钱打针吃药,医治沉疴新疾,数月之后便辞别了人世。 临终前,张逸仙有气无力地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想到,自己提着脑袋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不是共产党的人了……” 姥爷去世已经好多年了,令我自己也感到惊异的是,姥爷和他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从我心中淡漠。在我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我甚至觉得,姥爷的形象反倒比我少年时候听舅舅讲述时更清晰、更真实。同时也领悟了舅舅讲述时的那种神情。特别是姥爷——张逸仙——古斯达夫的临终遗言令我心颤:“我没想到,自己提着脑袋干了一辈子的革命最后竟不是共产党的人了!” 是懊悔?绝不是;是委屈?或许有,但是我想,那是一种遗憾——壮志未酬的遗憾,不被自己人承认和理解的遗憾。 然而,无论承认和理解与否,历史就是历史。或许因为表述方便的需要,我们长长会把历史涂以颜色:红色的、白色的,或者其它什么颜色。其实,历史无色,它应该清澈透明,如深秋里的一泓潭水,明白如镜,波澜不惊,深邃却能一眼见底。我想,张逸仙和他的战友们一定企望这样的历史,不仅透彻过去,还能映照今天,甚至未来。 责编:张海亮审核:谭鹏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