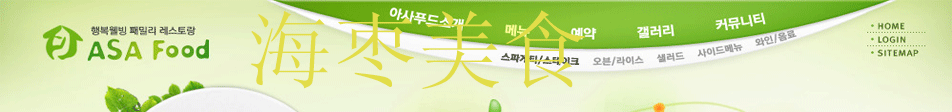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年,生病的高尔基想起了已经逝世10年的好友契诃夫的葬礼。 那天的人们以为火车运回来的棺材是从满洲里来的凯勒尔将军,为他奏起了军乐送葬。当发现弄错了的时候,契诃夫这个曾经受到莫斯科“温柔爱戴”的作家,最后也不过让无动于衷的人群引起一阵傻笑。 只有他的母亲与妻子,在这个人群中相互搀扶,那是契诃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两个人。 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以这样的方式,给《契诃夫的一生》这本书做了一个别样的结尾。当合上书面的时候,读者才明白,原来那个散发着月亮般清辉的孤独背影,是契诃夫,也是内米洛夫斯基。 内米洛夫斯基出生的次年,契诃夫逝世,她穿透三十年的时光迷雾,走进前辈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一个孤独而亲切的契诃夫。这个一生都避免描述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内米洛夫斯基,只给契诃夫一人书写了真人传奇。因为她笔下那个孤独的契诃夫,也是她自己。如果时间重叠,他俩可以成为心意相通的朋友。 《契诃夫的一生》封面作者花了一半章节写了契诃夫的家庭与成长,一半章节写了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俄罗斯影响力巨大的作家,是因为契诃夫的家庭与成长背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写作思想与创作特点。 契诃夫的作品曾不断地被拿来和莫泊桑比较,被同行轻蔑地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走了运的年轻文人”,就连阿赫玛托娃也说他的小说是一个“泥浆色世界”,缺乏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缺乏深度、厚重和崇高……剑光从未闪烁。 而在内米洛夫斯基眼里,这些不公正的评判以及在文学道路上的不被理解,反而使契诃夫更加成熟,在精神上更加独立。 只有作者才能真正看透这个叙述始终平静,不大发议论、不文艺、不激情背后的契诃夫,拥有着怎样一个灵魂。 孤独,是契诃夫和内米洛夫斯基一生都未停止过的经历 出生于穷人家的契诃夫和富人家的内米洛夫斯基尽管家庭背景不同,但他们都一生经历着孤独,没有人能读懂他们的内心,只有通过文字来疏解这种孤寂。 01契诃夫:月亮般的邻家大哥 安东·契诃夫的父亲是一个翻身农奴的儿子,他笃信上帝,开着一家生意不太好的杂货铺,以此养活一家八口人。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在现实中越是屈从于苦难的生活,他就在自已家的王国里独断专行。 他时不时会打骂软弱的母亲,对家人也是拳打脚踢,寒冷的冬夜整夜让孩子们给他看店,一家人每天都生活在鸡飞狗跳中。 作为五男一女中的第三子,契诃夫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安静地长大,他永远尊重父亲,时刻关心兄长,爱护幼弟幼妹。他几乎一辈子都笼罩在这样的情感中。 他了解幼年生活的塔甘罗格小镇人们的贫穷,也深受家庭暴力之苦。这也是他未来小说的一个写作源泉。 后来,老家的房子卖掉了,全家人租住在莫斯科的地下室。哥哥们去上大学的时候衣服鞋子都没有,在深寒的冬日里冻得瑟瑟发抖。 懂事的契诃夫为了养活家人,从18岁开始就拼命地写稿,为了能快速赚到现钱,他几乎只写短篇小说,一篇又一篇。 拿到稿费不是去给闯祸的大哥买太平,就是去支持想当画家而颓废的二哥继续追梦,或者给读书的弟弟置办衣服以免冬日里冻坏。家里的房租日用开销,赡养父母,样样都是他承担。他就是契诃夫家的顶梁柱。 一度他的写作环境是:上一刻父亲大声的祈祷声,下一刻就被孩子不停哭闹、邻居们叫骂的声音所围绕。等周围安静下来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孤灯下的契诃夫还在奋笔写作,因为家里要花的钱还等着明天的稿费。 但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抛弃家人。穷怕了的他,在他终于买下自己的地产和房子时,也没忘了接一大家子的兄弟姐妹们去他的房子里居住。他对于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是那样的开心,以至于迅速地变身为园艺爱好者,种树,养花、铺路、去林子里采蘑菇,装点自己的家。 作为医生的他,知道自己有病在身,负担着整个家庭,经济也拮据,活不过四十,不想害了人家姑娘。 但当一个生机勃勃、刚毅果决的漂亮女人,来到性情温和的契诃夫身边时,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好斗的力量,青春的热情以及对生活的爱。 这位姑娘是契诃夫话剧《海鸥》的主演奥利加·克尼碧尔。年5月,两人结了婚,3年后,作家去世。 就是这样一个温柔如水的男子,安静而坚韧地爱护着身边每一个人,看着都让人无比心疼。契诃夫是一个务实的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实实在在。这种心态,反射到了他的作品中。他从不在作品中构建虚幻,也不进行自我鞭挞,而是把一切落实到实处。 在他一生中,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了解他内心的孤独。他生活中温柔善良,作品也是平静而克制,但所有看完作品的读者,都会因之而被深深震撼。 内米洛夫斯基借用批评家布宁的话说: “即使在最亲近他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曾经真正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全部想法。” 也许契诃夫并不想让别人了解自己,为了保护好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迷失和绝望的灵魂。 作者笔下的契诃夫,不再是搜索词条里一个冷冰冰的存在,而是一个能击中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人。 才华横溢而早逝的二哥给契诃夫画的画像02内米洛夫斯基:冷血与热爱 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俄国基辅的一个犹太银行家家庭。她无需发愁生计,每天家里面仆妇围绕,她一个眼神就马上有佣人来服侍。吃个早饭有三个佣人来服务:一个倒牛奶,一个挑牛奶皮,一个用金剪刀剪开鸡蛋壳。 但这个家对于她来讲,是一个金丝笼。她身边看似从没缺人,但她内心是孤独的。学习是妈妈请的家庭教师,她不用上学,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只有各种各样的家庭老师轮流着给她上课。 父亲忙于赚钱,毫无空闲给她一点父爱;母亲一个接一个地找情人,带女儿出去度假,母女俩都住不同的度假村,以免被撞上。 她从小就在这样一种父爱、母爱同时缺失、没有同龄人交际的环境中长大,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孤独。 她怕自己受基因的影响,走上母亲的那种无节的浪荡生活,拼命地保持洁身自好的生活。 年十月革命前夕,她在窗口冷静而冰冷地看着看门人被暴徒所屠杀,这样的心理配置,注定她成为一个冷静的写实者。 年,作为犹太人在芬兰避难时,她开始写小说,拼命地用这种方式来治愈自己。后又逃到了法国,在法国定居。 年,她预感到对犹太人的绳索越来越紧,一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即将会发生。她冷静地提前写好了遗嘱,详细而周到,包括孩子的生活费安排和饮食禁忌。 同年7月,39岁的内米洛夫斯基由于是“没有国籍的犹太人”,被法国警方根据德国占领军的规定逮捕。被带走前,她对两个女儿说:“我现在要出门旅行一趟。” 一个月后死在集中营里。 期间,她的丈夫也在集中营死去。无法想象她在集中营的那一个月,是怎样熬过人生最后那段悲怆日子的。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热爱写作的她写了《大卫·格德尔》、《秋之蝇》、《孤独之酒》、《依莎贝尔》、《狗与狼》等极具心灵震憾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总是能感受到那种一望无际的孤独与冷漠,而且是无可救赎的,内米洛夫斯基尝试在荒凉的内心世界中寻找出路,却始终无法走出这种从小到大根植于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可见,决定一个人的孤独,与贫富无关。穷人和富人各有各的孤独,环境虽然不同,但孤独的本质却是相同的,并且这种孤独无时无刻地伴随着日常生活。也只有相互孤独的人,才能深深地参透彼此内心深处那不可被人问津的荒凉。 内米洛夫斯基评价契诃夫的那种孤独,是这样讲的: “是否因为他太过聪明、太过清醒,所以缺乏爱的能力?在他的心中,他的生活中,是否有这样一种矛盾情结,迫使他向冷漠的人们交付出过多的自己,而后,又匆促地收回去?他是否是痛苦地克制着,隐藏起自己的想法?” 这何尝又不是内米洛夫斯基本人呢? 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懂一个人,不一定是同一生活环境,也不一定是同一时代 01悲伤的契诃夫和悲观的莫泊桑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俄罗斯评论家们想讨好契诃夫,常常将莫泊桑相提并论。但内米洛夫斯基眼中的契诃夫与莫泊桑是截然不同的。 虽然两人都是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虽然都是穷小子出身,虽然都是才华横溢,前半段人生的遭遇基本相似,一直都在贫穷中摸爬滚打,但他们的小说差异性还是相当大的。 莫泊桑的故事太过完美,是精心设计过的故事,过于机械化。 比如《项链》,这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相当具有故事性。小公务员的妻子玛蒂尔德为炫耀自己的美丽,向朋友借了一串钻石项链,去参加一个晚会。不料,项链在回家途中不慎丢失。她只得借钱买了新项链还给朋友。为了偿还债务,她节衣缩食,为别人打短工,整整劳苦了10年,最后碰到那个朋友,朋友说:“唉,可怜的玛蒂尔德,我那一串项链是假的,顶多值法郎。。。”假的!而玛蒂尔德为了这一串破项链,花了十年时间来偿还那串项链的钱。 读者看完这个故事,打心眼里佩服作家讲故事的水平。莫泊桑特别喜欢在故事最后用一句话,让故事反转,这些话就像一支箭一样直插入读者的脑海中。 然而,过于刻意的制造情节冲突,凸显主人公时,反而会弱化故事的真实性,看似很符合逻辑,却使小说变得贫乏,因为缺少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 契诃夫的小说追求故事的流动感,因为他深知现实是复杂、美丽、深刻的,故事要建立在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此在到彼在,从欢乐到痛苦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 他力图通过短短的几页纸,把许多人类体验包含在内。 比如《哀伤》,一个失去儿子的马车夫,他无法向任何人倾诉丧子这痛,最后只能讲给自己的马听。没有什么大事,甚至没有最小的事件。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命运。 平民百姓不都是这样嘛,太阳底下无新鲜事,读者从这些平凡庸碌的生活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小说中人物的内在。所以他的小说是鲜活的,具有人性化的不完美。 内米洛夫斯基最后给予两人的评价是: “莫泊桑的人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们贫穷、衰老或生病,他们绝望的理由都是外部的。而在契诃夫笔下,一个人痛苦的原因是,在他眼里,生活没有任何意义。” 契诃夫的小说是悲伤,莫泊桑是悲观。 契诃夫02托尔斯泰的“应该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和契诃夫的“从不教导别人怎么做”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伟大的托尔斯泰将契诃夫视为才华横溢大有前途的后起才俊,而他在契诃夫心目中,就是文坛泰斗,让人仰慕与敬佩。两人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一种“意识浸润液”,就是说,他的作品像刚钓上来的鱼,带着水气和鲜活感,从意识深处钓出来的观念,场景,人物。 它是一种“有机现实的还原”,取决于心的激情和智慧的激情。当他沉溺于前者就是好故事好情节,当溺于后者时,就是说理狂人。大道理如洪水般涌来,滔滔不绝。他告诉你应该是这么做,而不是那么做的。 契诃夫一度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像托尔斯泰一样,波澜壮阔、大气雄浑,他也尝试着用偶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最后总是那样的空洞和苍白。 想想这两个人,一个是出身高贵的伯爵,反智、热爱农民,厌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及城市文明,而另一个,深受暴力家庭的影响,看着被现实毁掉的两个富有才华的哥哥,常年住在地下室,混迹于市侩,被庸俗气息包裹着。 那是拥有万贯家财的托尔斯泰无法理解的世界,而契诃夫也无法精准地描述出他所不熟悉的上流社会,谁都无法模仿和复制。 当契诃夫参透自己在描绘所不熟悉的中产以上阶级的人物时,自己的那种胆怯是无法避免的,而他,永远也不会有托尔斯泰的宽裕自如,倒不如写自己熟悉的世界。 后来,契诃夫的写作会以一种平静的幻灭感渗透在作品中,有时候,它们带着独特、清醒、温柔、安宁,以一种淡漠的冷静,在读者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有这些就够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有时不教导,比教导更有意义。 在内米洛夫斯基看来托尔斯泰有宗教信仰的自暖动力,而契诃夫的灵魂从来没有被暖起来过,他是普通人,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总被生活的脚步赶得气喘吁吁。 契诃夫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描绘自己的人生和写作进程, 开头总是满满当当的许诺,中段便变得皱巴巴怯生生,到结尾烟花一场。 他不再赞同托尔斯泰的道德自我完善理论,他也不再认同这是治愈一切痛苦的惟一解药。从此后,他们渐行渐远。 契诃夫和托尔斯泰在契诃夫病逝的那天晚上,当妻子将冰块放在涉死病人的胸口上时,他轻轻地推开了: “没有人把冰块放在空洞的心口。。。” 而内米洛夫斯基曾试着躲避那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追迫,但在最大灾难来临时,她没有再选择逃亡,从容被法国宪兵带走,最后死在集中营。 那时,她一定也和契诃夫同感,即:坦然接受是对于命运最好的反抗。 当灵魂彼此重叠到没有缝隙的程度,任何形式意义上的相遇都不再重要了。 月亮的清辉下,只剩下那些“混合着玩笑、伤感和平静的失望”式的契诃夫人物,以及内米洛夫斯基的人物,借着微光,慢慢照亮这世上喁喁独行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