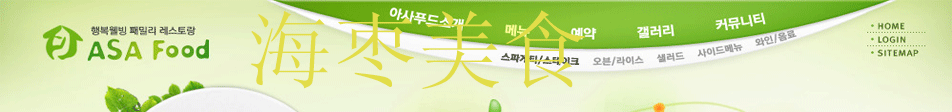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 尽管30多年前离开重庆后,也经常出差重庆,但来去匆匆,很少细品重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 最近又去重庆,下榻江北嘴,面对朝天门。一大早,淫雨霏霏中沿嘉陵江散步,细观两岸重峦叠嶂的建筑,下半城的吊脚楼一扫而空(抗战时期下江人逃难时盖的简易居屋,用木头依山沿两江而建)。一时间,陈事旧物,直闯脑门。那时,出菜园坝火车站,极目望龙门,吊脚楼呼啦啦奔来眼底。从旅游角度看,那消失的吊脚楼可是重庆的一景啊!只是好看不好住,我有个同学的家就在这种建筑里,我上去过,走起来摇摇晃晃,听起来叽叽咕咕,怪危险的。远眺江上,发现两江上有太多的桥。扫眼过去,嘉陵江这边就有三、四座,长江那边也有好几座,有的还是双层桥,上汽车,下轻轨。我查百度数据,年重庆市城区内有27座桥,可30多年前重庆市区仅有两座分别横架于长江上的重庆长江大桥和嘉陵江上的嘉陵江大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取得成功后,改革向城市迈进。在我国大城市的综合改革中,最早踩下脚印的就是重庆人。30多年前,我是经济日报驻重庆记者,亲眼目睹并记录了重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风风雨雨。写过一些文章。往事并不如烟:年6月,重庆自告奋勇提出试点厂长负责制,市委市政府确定了28家企业首先试行厂长负责制,试点效果很好,重庆市委市政府迅速向全市推开。一年半后,重庆已有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它们的产值和利润分别占重庆市的80%。年3月,经济日报刊登了我写的《路,是这样走过来的》通讯稿,记录了这段历史。年重庆钢铁公司在全国首家发行企业债券,采取了直接融资方式,探索性地改变了中国过去只能向银行贷款的传统融资模式。这个经验被我写成《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一文。年重庆饭店中外合资,重庆热情邀请美国人邓贝来当总经理,后因意见不合邓贝被中方大股东解雇,此事反映了我国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不适应,为此我写了《洋经理为什么被辞退?》一文,见报后引起讨论。年“价格改革闯关”中的“双轨制”弊端突出,为此我写了《一个“倒爷”向市委书记透露秘密》的对话录等等。这次故地重游,细看重庆增加了这么多的桥,才觉得我在30多年前发表于经济日报《桥,山城人的希望》这篇文章,把桥作为重庆人的希望提出来,没有太跑调,自认为还是抓住了当时重庆经济民生中的关键问题。 重庆桥的历史变迁,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过去重庆桥太少,记者在全市采访很费劲。长江和嘉陵江把市中区(现在叫渝中区)半岛与江北区和南岸区分割开来。两岸的人,相互往来,天堑锁钥,要么过桥,要么摆渡,十分艰难。和全国一样,那时重庆也穷,没钱修太多的桥。因此,不仅仅是我们采访不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非常不便。 那时重庆仅有两座桥,一座是年建成通车,从渝中区上清寺连接江北区华新街的牛角沱嘉陵江大桥,过去就叫嘉陵江大桥。一座是年建成通车的重庆长江大桥,连接渝中区石板坡和南岸区南坪,现在叫石板坡长江大桥。在仅有两座桥的年代里,两岸都是我当年采访经常要跑的地方。还记得40年前重庆长江大桥建桥时有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说是著名雕塑家叶毓山等人为大桥做了一组以男女人体方式表现春夏秋冬的雕塑,采取了裸体的人物造型。这组雕塑的设计样稿一经公开,舆论哗然,议论纷纷。那时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怎么能让人不穿衣服就站在桥头呢?”,“多羞人”!最后,经过雕塑家刘开渠、美学家王朝文等组织专家讨论。作为妥协,艺术家们被迫给这组雕塑套上一层“薄纱”,算是披件衣裳,蒙一下羞,雕塑才得以落成。如今,这些曾经裸体的人物仍然披着“薄纱”坚守桥头。 重庆交通不便古已有之,但有水码头。李白早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长叹,也有“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惬意。18世纪重庆开始建造外省商人聚集的会馆,有湖广会馆等8省之多。19世纪末,英国人顺长江进入重庆并开埠,山城成为商业贸易大码头。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卢作孚的船队通过川江抢救战时物资大撤退(重钢的张之洞洋务运动时期的“汉阳造”等设备,就是从武汉抢运到重庆的)。新中国的60年代,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镇,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从外省转移来一批军工制造业。重庆处于崇山峻岭之中,怀抱于两江之内,可凭借天险拒敌于千里之外。易守难攻、偏安一隅的重庆,交通不便也许是个有利因素。但改革开放后,这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极为不利的条件了。重庆想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积极争取改革开放走在前,勇立潮头敢为先。年,重庆市被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为第一家计划单列城市,在四川省辖下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由此,重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排头兵。中央希望重庆在改革中大胆往前闯。年经济日报把我从北京派到重庆常驻,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采访报道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向全国推广。 前面提到那篇关于重庆“桥”的报道,是有感于重庆基础设施落后影响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作。回想起年底参加重庆第三座桥的通车典礼场景。在一个霏霏细雨的早上,重庆市党、政领导几乎全部都聚集在一座刚刚落成的大桥上,参加那个历时三年建设、投资1.1个亿的嘉陵江石门大桥通车剪彩仪式。当下的年轻人也许会问,重庆市区今天已经拥有20多座大桥,那段往事何以值得如此这般隆重?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重庆过去的历史,在国外有较高的知名度,因而成为计划单列市后,许多外国人纷纷来重庆考察投资。采访中我听到最多的是他们对重庆基础设施的抱怨。当时来重庆考察商机的一位叫法·比恩的美国商人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说:在重庆生活很不容易,交通太不方便了,在“时间就是金钱”的西方价值观里,重庆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当时重庆的一位官员说,重庆特大的城市,狭小的交通,不知挤走了多少兴致勃勃而来的投资者。没有起码的投资环境,留不住人。桥,是畅通重庆交通网络、发展经济、促进贸易的关键。因此,在参加了上面说的大桥剪彩仪式后,我迅速写出了《桥,山城人的希望》的通讯,经济日报在年1月10日头版刊登了。第二天《重庆日报》在一版全文转载,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为什么当地报纸这么看重这篇报道?我估计是,这篇文章说出了重庆人的心声。因为作为“两江夹半岛”的山城重庆来说,桥,对于沟联交通、畅通物流、发展经济、方便民生太重要了。我在文中写道:“它的修通连接了重庆市区被天堑隔断的汉(口)渝公路和成(都)渝公路,沟通了重庆这个半岛型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形成了重庆市交通网络的西半环。使过去要绕行16公里的车辆可以长驱直入,1年仅节省汽油的价值就达万元……。这座大桥通车的意义,远不在于经济上,而是在它的象征意义上:它的建成通车表明重庆市政府为彻底改变重庆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的状态和决心开始得以体现”。重庆在建设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资金筹集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通过市场来进行了,这在30多年前是有改革领先意义的探索。当初重庆迈出的第一步,属于“第一个吃螃蟹”者,他们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有偿使用,向社会筹集建设资金。尽管那时候看法各异,争论不止,但重庆市政府还是尝试着迈开了步子。我写道:“从年起,他们先后出台了征收城市综合配套费,预收嘉陵江石门大桥过桥费,收取长江、嘉陵江过桥费、土地使用费、建立公用事业发展基金、城市服务费、发放道路桥梁债券等政策。靠这些政策,重庆市政府筹集到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占前5年全市市政建设总投资的50%以上”。这些早期改革开放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深化,极大地推进了重庆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了重庆人的生活水平,山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大幅提升。今天,朝天门到大坪几十平方公里的半岛上就有9座桥,主城区有20多座大桥,整个重庆行政区域里有1.3万座桥,重庆被称为中国的“桥都”,名副其实的桥梁博物馆。不仅仅是桥,其他基础设施发展也很快。现在,重庆交通已经四通八达,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西部大都市,外地、外资企业不少,物畅其流。直通欧洲的渝新欧班列已经开通7年,自开通以来已经通行多班。从重庆开出,历经16天,经过新疆穿越中亚直达德国杜伊斯堡。在西向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高速发展的同时,重庆多条国际物流通道也逐渐形成。重庆向南直达东盟。重庆向北联通中俄。渝满俄班列从重庆出发,北上经满洲里出境,横越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班列已于年实现常态化开行,累计已开行多班。重庆人修桥铺路、筑巢引凤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效果。 上百度网查询知悉:重庆年GDP仅为亿元,年GDP接近2万亿元,比30多年前增长了多倍。年上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在年中国城市最佳商业百强榜中,重庆位列第四。 写完《桥,山城人的希望》这篇报道不久,我就离开了重庆回到北京。一晃30多年。 再次细观重庆,作为曾经在此工作和生活过4年多的人,由桥而带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扑面而来。 从百度地图上看,无数的桥把过去两江割断的山城完全网格化了,桥在两江上穿梭连接起来的网状道路交通,如人体之经络覆盖了重庆的山山水水,重庆经济社会活动的血脉通畅了!把地图上的桥蒙住看,重庆的整个交通网络全部中断。古人云,往来不穷谓之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重庆的“痛”的点已被“桥”疏通。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的领导者在城市建设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一届地坚持架桥铺路,打通了重庆的“奇经八脉”。贸易舒服了,经济舒服了,群众舒服了,社会舒服了。对于桥的建设,重庆老百姓赞叹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