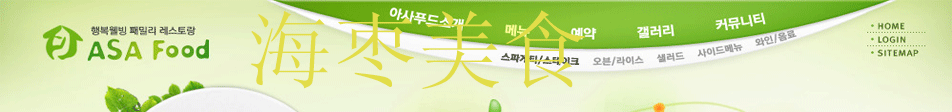|
“你知道内蒙古的牛啥时候最瘦吗?” 对面的吕阳明看着我,悠悠的东北话隔着羊肉汤锅的雾气飘过来。 “冬天还不是最瘦的时候,春天把黄草吃完,那绿草刚出来的时候,它是最瘦的。为什么呢那草刚刚长出来,绿绿的短短一截儿,那牛用舌头添呐但够不着。它抬头一看,诶?前面都绿绿的。它觉得那儿肯定更长一些,于是它就不停地往前跑。人就是这样,总觉得远处的会更好。闯关东那些人也是一样。家乡发了水遭了灾,一个人过来了,完了写信回老家:哎呀东北好,能生活。然后大家就都来了。那是一个最简单的需要啊,就是为了活。” 到达满洲里的第一晚,我们坐在一家蒙古菜餐馆里涮着羊肉。面容俊朗、身形挺直的吕先生供职于满洲里海关,是我此行采访的第一个当地人。他热爱历史,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赠我的这本小说集《芦花飘荡》收录了很多边城背景下的短篇故事,包括这些闪着光的句子: “北方这座小城太小了,我们不到一个上午就找遍了它的各个角落。” “夏季的风吹过无边的草原和旷野,在水面上吹出一层层细密的波纹。正午的太阳就在这水面上荡漾着细碎的波光。” ▲午后,透过窗户看出去,外面是红顶或蓝顶的民居。 满洲里东依兴安岭,南濒达赉湖(又名呼伦湖),北邻俄罗斯联邦的后贝加尔边疆区,西近蒙古国的东方省。全市总面积平方公里,人口30万,蒙古、汉、回、满、俄罗斯等民族在此居住。辖区内有54公里长的国境线,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沿边陆路口岸。这些资料都没来得及解答我一个疑问,我把它抛给了吕先生。 “你们比较认同自己是哪里的呢?” “东北人说我们是内蒙的,内蒙人说我们是东北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平时咱们聊天儿,你家是哪儿的,河北的,喔,我是山东的。这都是唠嗑儿。人家不会说:山东的?唉?咋来的啊?咋跑这儿来了呐?” 在场的朋友抑制不住笑声。吕先生做了一个典型东北风味的总结: |